陈东琪教授简介:
陈东琪教授,195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,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后,留该院经济研究所工作; 199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;1989-1990年和1992-1993年,先后赴美哈佛大学、贝克莱加州大学等院校进修货币金融理论和从事博士后研究;1993年晋升为研究员;1994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;1995-1999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,1999-2001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,2002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、党委书记。现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。
陈东琪教授两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,两度获国家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功奖,1989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,多次获其他国家级奖项,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1996年进入国家七部委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。1996年入选《中国中青年新闻人物年鉴》,1997年获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,现为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”成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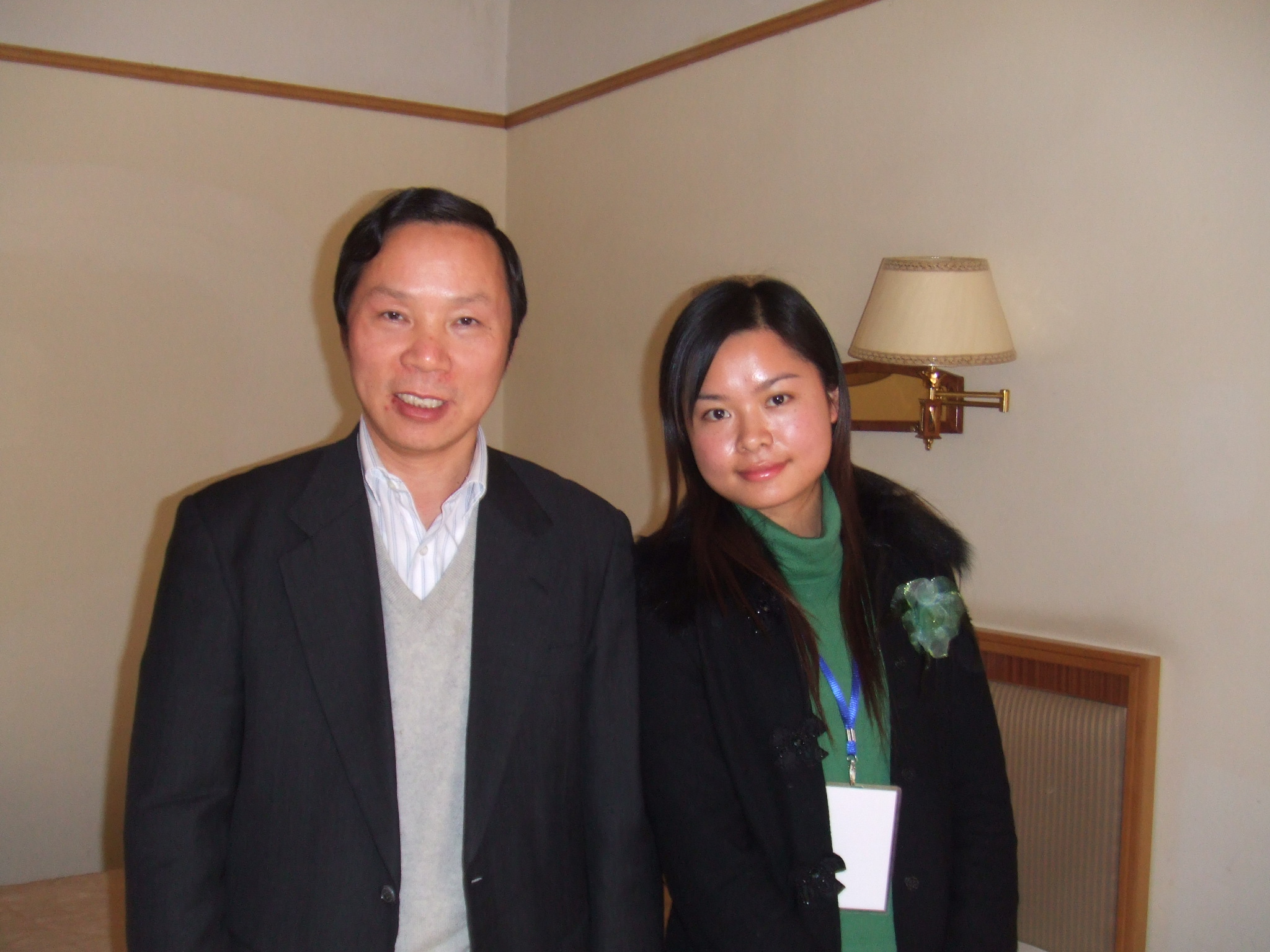
记者:陈教授,您好!我们是betway必威的学生记者,欢迎您来到betway必威,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我们知道您是多个城市政府的经济顾问,您曾经为柳州提了自主创新八条,又是济南“十一五”规划专家委员会主任。您认为它们的发展历程对湖北、对武汉来说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?您认为武汉加快发展、实现中部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?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您的看法?
陈东琪:武汉应该是我们中部崛起的重镇,第三产业在武汉发展的水平要比湖北其他地区要好些。对于湖北全省来讲,它是一个农业大省,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比较高,湖北和武汉的经济结构不一样。武汉主要发展的是工业和服务业。武汉不是有光谷吗?武汉的信息产业也不错啊。工业方面,武汉市这两年的汽车产业发展也很快。武汉的新材料、化学、化工等行业也不错。武汉的产业比较齐全,特别是工业领域,有传统的工业,也有现代的产业;有劳动密集型的,也有资本技术密集型的。所以,武汉的发展既有老的工业城市的优势,又有新兴的工业优势特别是光学方面。武汉作为湖北的省会城市,从中部崛起的角度来讲,地理位置很重要。武汉、长沙、南昌是一个大的金三角,所以在中部六省里面,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地位非常重要。
武汉也有很好的教育资源优势,湖北的大学也比较多,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武汉。betway必威、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都不错,武汉的教育资源很好。这意味着武汉经济未来的发展还是有很大优势的。人力资源对经济的推动会越来越重要。还有一点,武汉人的消费需求还可以,就是武汉人比较爱消费。加上武汉现在处在快速发展期,有着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,武汉的城市面貌、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在加快。
记者:作为一个中部城市,武汉除了优势,还有什么劣势?
陈东琪:任何地方都会有劣势,即使再好的地方也会有劣势。美国的纽约也有劣势。当然从区位角度来讲,现代经济的流动主要借助航空和海洋,尤其是海洋经济的发展使得沿海地区有更好的区位优势,内陆省份在全球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可能稍微处于下风。我们以前的经济是以江河为依托的经济,所以武汉沿着长江是很有优势的。但是海洋经济和江河经济相比,海洋经济的纽带更大。因此我们国家开始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在沿海地区。但当海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,东南沿海也有个成本上升的问题,另外它也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,同时它还面临着一个资源问题。从这三个方面来讲,中部地区有优势,武汉也有优势。一个是它的成本比较低,劳动力成本和工资水平都比较低。第二个是它的需求还是很大的。中部地区六省的人都很多,比如湖北现在有将近6000万人口吧。武汉人口也很多,加上人均收入水平开始提高,所以武汉的需求容量还是很大的。第三个中部地区有资源优势,不仅仅是农业的资源、工业的矿藏资源,而且还有人力资源。至于劣势,在于内陆城市开放的紧迫感意识不是很强,内陆普遍存在“小富即安”的思想,容易满足,这可能是个很大劣势。
记者:谢谢您对武汉的关注,您将在“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”的论坛上演讲,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的研究成果吗?
陈东琪:我讲的是关于2007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,战略调整和政策取向的问题。
记者:陈教授,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2008年前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,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好了,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?
陈东琪:拐点是什么意思?是从一种趋势向另一种趋势转折,从上升趋势向下降趋势转换是拐点,还是发展速度由很快到变慢是拐点呢?我对拐点这个判断表示质疑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一点:
第一,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还很强。你看城市化,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人口转移,我国现在城市人口每一年增加两千万左右。近十年我们增加2.2亿城市人口,农村人口是减少1.14亿,每一年减少一千多万。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城市发展有更大的投资,也意味着整体经济有更大的发展。
第二,我们现在的人口还处于增加期,我们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。
第三,我们国家科技进步加快,劳动生产率提高,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的提高,国民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。
第四,我们现在提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,扩大了发展的空间。我们提出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,社会事业比如说公众医疗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等都获得很大的发展,这些公共事业的发展能带来较强的生产效应。
第五,我们现在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、多层次的。我们贸易扩展的能力很强,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能较快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。
第六,入世以后我们市场开放,资本流入、引进来和走出去,这都会把中国经济搞活,特别是金融市场开放。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能较快地促进经济增长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会给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很强的预期。投资、消费的预期都比较强。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还是很强劲的。当然也可能有个不确定性因素,我们连续四年增长10%以上,是不是还会加速?估计我们的宏观调控会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,不是说一定要形成一个拐点后再到一个下降通道里去。我想无论是从客观的生产因素来看还是从宏观调控的主观意愿来讲,很难说是一个拐点。就是说有点上升趋势,把它拉到下降通道里去,至少也看不到这个倾向。所以拐点论还得检验,我先不说它对不对。
记者:中国竞争力的排名比上一年略有下滑,现在是50多名,您如何看待?
陈东琪:这样的变动是正常的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力是不断提升的,比如说我们产品的竞争情况。我们的出口增长非常大,净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,顺差很大,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不断上升,当然原来我们产品的低价优势会慢慢有所减少,但是我们的产品在提价以后也会有很大的出口潜力。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产品的构成品质都在改善,这当然影响竞争力。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因素,比如一些法律问题和生态问题。所以我觉得不能看一个时间点,而要看一个长期的趋势。我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比较乐观的。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黄金期,一个繁荣的延续时间最长的时期。
记者:今年12月11日,我国入世五年的过渡期保护结束。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,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,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业有什么影响?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呢?
陈东琪:不能算是全面进入,12月11号是放开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限制,就是说可以吸纳存款,原来是不能吸纳存款的。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比较脆弱,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还要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发展,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要为我们的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。至于放开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挑战,肯定会的。
首先,外资银行具有先进的管理水平、管理经验,强大的资金实力,高效率的全球资金调动能力,这样的金融机构的进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。我们把吸纳人民币存款的门打开了,吸纳人民币存款的门槛限制在100万元以上。实际上外资银行的客户就固定在国内的富人群体。国内的富人,有可能去外资银行存款,那国内的银行会失去很多业务,这是很大的挑战。其次,会产生更多的股权收购,尤其是对银行的股权收购,因为它有资金实力。第三是会对我们整个银行产权产权制度造成冲击,我们目前的股份制改革还需深入。
记者:有人说您1999年以前是学者的身份,99年以后是政策制定者的身份。您认为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学术上有所成就自成一派重要呢,还是为政府出谋划策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?
陈东琪:都重要,学院派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,尽管他们不会马上影响经济决策。但是他们研究的理论可能影响的是中长期。他们履行了对社会的责任,对广大百姓的责任。我们既需要学院派也需要非学院派的学者。毕竟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靠一年一年走出来的,是靠一项一项政策的推动。那么这些政策能不能更科学一些,更符合老百姓和客观社会的发展一些,这需要我们的研究。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就是一个研究部门,我的岗位决定了我的职责,当然也是我的兴趣,我的体会是中国经济特别是宏观调控的要求更为迫切,让我们的经济既快又稳地发展,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共性之一吧。反正这两条道路各自有特点,各有需要。大学里面对经济运行的实感,不像我们那么快,那么直接。所以如果要尽快决策的话,我们的决策更接近现实些。但是,学校研究也有它的好处,会更冷静些、更长远些、更客观些,所以各有优势,两个是互相互补。其实发达国家也有类似情况,你看有一些学院是这样的,像芝加哥学派,货币主义,后来也影响到了决策。按照西方的观念来讲,经济和哲学社会科学还不完全一样,经济更具有实用性,也就是说,能直接积极主动地干扰影响现实。反过来,经济又受到社会的影响和推动,具有政策性。所以你看那些经济学家,美国的也好,欧洲的也好,都是决策前沿的。这两个我觉得各有优势,不能说谁好,谁不好,谁重要,谁不重要。有时候学院派重要,学院派有冷静的思维;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,政策的决定就很重要了。如果说我这个重要,他那个不重要,大家都不搞研究了,那明天政策搞错了怎么办?所以还是需要学院派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的。
记者:我们知道您是很多大学的兼职教授,那怎么看待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呢?
陈东琪:中国的教育整体相对于经济来讲是滞后的,中国的经济发展快而且发展势头非常好。在全世界的影响非常好。但是中国的教育就比较滞后的。原因有很多方面,一个方面当然是教育体制的历史关系。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、金融业改革滞后。当然现在也改革了很多。我们也出现了在全世界排名比较好的一些大学,像北京大学排在第14位吧。betway必威也不错。一些合并后的大学也很好,教育虽然也有一定的改革,包括教育的内容、培养体制、教师队伍的流动,但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讲还是滞后的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学生资源经过学校学习以后,能不能变成好的人力资本。就是说我们的学生进入学校以后学习四年本科,三年研究生,三年博士,出来以后与实际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还是有一定距离,为什么呢?因为我们大学教育偏重知识,而对于能力的培养不是很重视。作为学生家长,作为旁观者,作为研究者,我感到我们的学生资源在全世界应该是比较成功的。初中、高中,特别是初中之前,尽管中国式教育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它相对于全世界来讲应试教育还是很成功的,我们学生考试很厉害,说明他们学的知识还是很多的。尽管他能力还不够。所以我们培养的中学生参加世界知名大学的考试,成绩还是很不错的,但是大学生毕业出来以后和世界上的大学生整体水平相比,能力上就落后了。为什么呢?比较好的中学生资源进入大学以后,四年内忽视了对能力的培养,更多的是知识的扩大。其实在现代信息条件下,简单知识的传授,不要花很多时间,学生就很容易学会了。这本书没有看不知道,一看就很容易知道,你花一年或几年学的东西,他花3个月就学会了,剩下的9个月他可以去干别的事情,去了解社会,去培养能力、去冒险、去创新、去设计。所以我感觉我们的学生老是背书,抄书,回忆以前学过的知识,不要这样。现代企业随时发生变化,原理很重要,但是原理和应用相比,应用和实际行动更重要。现代大学生不能总是跟着老师跑,整天忙着考试、背书,也不能整天为了成绩而竞争。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。我们培养的学生要能够放在实际部门、放在跨国式的研究机构。当然,国内也有大学后培训,我们的同济大学现在就在搞这个。学生学了四年知识以后,再有一段时间是岗位培训时间。国外都是大公司承担大学后教育问题。但是我们可贵的年轻的人力资源上了大学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。我自己就有深切感受,我们培养的学生不少,每一年我们招生是500多万,毕业生是400多万。我国在校生就1600多万。韩国总人口4600万,美国人口3亿。我们在校生就是一两千万,应该说在全世界是打遍天下无敌手,那么多大学生,做软件还怕印度?可是在这方面就是竞争不过印度。不要看我们大学生统计数据那么多,那没用。至少从现实来讲,印度出的软件价值份额就是比我们高,我们往往去做资源加工,资源加工不是我们大学生,而是农民工在做。建筑业都是农民工在承担。所以我们讲的资源节约仅仅指的是自然资源、水土资源、矿产资源的节约,其实人力资源的节约更重要。所以我很欣赏你们这种采访方式,我一般不接受采访,我为什么接受你们采访呢?我对学生是很支持的。第一,学生有这种想法,有这种渴望就很不错;第二,经过一次一次的采访,能锻炼人。你不让人上台演出,怎么能让人当名演员呢?是不是?它总有个过程吧。就像爱迪生发明灯泡的灯丝,人家说他前面两千多次是失败,他说:“不对,我前面两千多次是寻找两千多种不可行的方案,也是成功”。就像走路一样,走了几次歪了以后,这次是走对了。前面也是个过程,也是一种经验。就像小孩一样,现在他不摔跤,肯定是他以前摔过跤,所以要给他摔跤的过程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,就要在大学里去尝试几次失败,几次的弯路,我们以后就不会走弯路了。
记者: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搞挫折教育?
陈东琪:(笑)不仅是挫折教育,也是一种能力教育。其实挫折也是一种能力的教育,包括反应的能力,调整的能力,能培养我们学生的创新意识。
记者:陈教授,您刚才讲了我们的农民向银行借不到款的事实。我们农民借不到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抵押品,而土地是最好的抵押品。如果我们深入进行土地产权改革,以某种方式给农民更多的土地使用权或者转让权,土地能够用来抵押的话,是不是能够帮助农民获得银行贷款?这种办法可行吗?
陈东琪:是一种土地担保吧。这是一个方面。其实农民贷不贷到款,不是农民一方的问题,贷款人和借款人两个方面都有问题。一个是贷款渠道不多,农民没有选择。我们的银行都是跟着利润跑。我们银行贷款的渠道应该更多一点,所以我们不能从农民一方来找原因。你刚才说农民没有担保,所以不给贷款,那是在为银行辩护。农民向银行贷不到款首先是供方的体制自身有问题。担保不一定是土地担保,还有很多担保,农民合作社里有建立互相担保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假定一个团体里有四个人,我们四个人形成一个合作社,你先支持我,下一次我来支持你,这也是一种信用担保方式。有很多方面你没去想,没去考虑。土地是一个方面,土地量也是一个方面。我们现在农村人均土地量很少。
记者:好像人均只有一亩地。
陈东琪:可能没有那么多,北方可能达到那个水平,南方就很少,湖北还可以,湖南是人均6分5的地。土地值不了多少钱。就算有地,三口之家一亩多地,农民的一亩三分地在现在不值什么钱的。如果我要搞一个十万的项目根本就搞不了。现在的土地是越到城市越值钱。北京的土地当然很值钱了,你到张家界去,那个土地值不值钱啊?没有钱。放到那里看都没人看。所以土地担保是一个方面。农村金融发展靠的是双方共同的努力。靠农民自己的能力肯定不行,农民哪有能力啊。
记者:是不是我们应该在农村大力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?
陈东琪:对,这是一个方面。这是我们政府管理的创新。这就好比学生也要有创新意识一样,政府的管理体制也要创新。整个国民的创新意识很重要。我们就是要创新,存款利息那么低,贷款利息那么高,银行赚存贷差就可以了,根本就没有创新的动力。我如果把存款利息提高,贷款利息降低,使银行的存贷差小,利润薄,就可以迫使银行创新。你们学生的创新压力也不是很强,尽管没有工作,但你们有父母在背后支持。你们哪有西方学生那种压力啊。西方学生不仅是找不到工作,他住房子,租房子都是靠自己,18岁以后父母从法律上就不管小孩了。中国孩子还有一个兜底的,那就是自己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年轻人的创新意识还是不强。因为这个制度不行,它不是一个竞争制度,发达国家有一个竞争的制度。同时发达国家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,只要我努力,我就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,我可以当议员,我还可以当教授。在中国不行,在中国非得多少年以后,老了长白胡子了才可以当教授,这个就不是一个创新体制。
记者:那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善激励创新体制?
陈东琪:反正就是说我们现在得一步一步来,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。现在我们中国挖掘的是土地、水、矿产资源的潜能,挖掘的不是人的潜能。中国最大的资本就是人力资源。潜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。潜能不在土地上。而我们现在经济增长的潜能就是挖土地。按我的讲法就是,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“地矿”,今后经济增长靠的主要是“脑矿”。从国际上的竞争来讲,美国的GDP有十三、四万亿,它服务业占70%以上,它实体经济支柱70%的经济增长靠的就是头脑。美国制造金融、制造保险概念、制造软件、制造标准、制造设计这些理念,卖的就是这些理念,卖标准、卖设计、卖软件,卖这些不要花大成本的东西。而我们卖的全是要能源的东西。我们和他们的竞争就是“地矿”和“脑矿”的竞争。根本就竞争不过。
记者:谢谢陈教授给我们这样的采访机会,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会期!(betway必威学生记者:梁婷 刘谦 吴志团)






